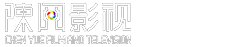NOTICE
公司動態(tài)
紀錄片攝像手法
閱讀次數(shù) [1670] 發(fā)布時間 :2018-12-24
由于電視的大眾化特性以及攝錄設(shè)備的小型化、普及化使拍攝紀錄片成為時下電視圈里的熱鬧行當,許多人摩拳擦掌,大起爐灶。
然而,中國電視紀錄片領(lǐng)域關(guān)于真實記錄的理論卻處在無休止的爭論中,紀錄片創(chuàng)作也陷入了多重困惑之中。“真實”與否仿佛成為了衡量紀錄片的生死線。拍攝中為了追求“真實”,畫面構(gòu)圖、景別、光線都很粗糙,鏡頭一路搖搖晃晃地走過,只要跟蹤拍攝,同期聲錄音,長鏡頭紀錄,就認為那是真實,就是紀錄片,這種“真實”觀實際上有待商榷。
一、現(xiàn)場紀錄的“一次性”能力
攝像師運用鏡頭的造型表現(xiàn)手段在尋像器里進行判斷取舍,展現(xiàn)現(xiàn)場事件的因果關(guān)系,矛盾沖突,以及對精彩瞬間的細節(jié)紀錄,使其負載的事件通過影像傳達出來,體現(xiàn)時代精神,塑造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這就要求攝像師在事件的場景中要有現(xiàn)場的觀察力和判斷力,而不是“現(xiàn)場”的機械記錄。“現(xiàn)場”拍攝要動而不亂,靜而不死。
攝像人員在進入現(xiàn)場之后對周圍的環(huán)境要有一個觀察和熟悉的過程,現(xiàn)場往往是紛繁復(fù)雜的,環(huán)境就是紀錄片的“場”,人和環(huán)境有著不可分割的情感和內(nèi)在的聯(lián)系。鏡頭選擇什么,怎樣選擇是直接體現(xiàn)著攝像師對事件觀察能力、審美能力的判斷與表達。
鏡頭記錄不是開機之后就等磁帶走完,事無巨細地記錄,而是要有針對性。景別要給那些最有趣味的事情,而不是一個大全景固定下來不動的記錄,觀眾受不了那種靜得發(fā)呆的長鏡頭。在一個相對的時間長度內(nèi),鏡頭內(nèi)部的信息量是有限的,這些信息直接關(guān)系著觀眾的觀看心理,如果出現(xiàn)了信息的缺乏和信息的不連貫,觀眾的觀看興趣就會下降,這樣,紀錄片本身意義的傳達和審美感知就會受到影響。一味追求“長鏡頭”的真實是紀錄片走向單調(diào)、枯燥的必然。單純堆砌生活場景,沒有選擇、提煉,就很容易使創(chuàng)作陷入“自然主義”的有影必錄的境地。攝像師對“長鏡頭”要抱一種客觀而理性的認識,如果“長鏡頭”中不足以體現(xiàn)一定的意義和信息,那么寧短勿長,寧缺毋濫。
二、攝像機的現(xiàn)場干擾
上世紀60年代的“真實電影”是用攝影機當“催化劑”,促進了某件事情的發(fā)生,甚至引導(dǎo)了事情的發(fā)展方向,在人類營造的環(huán)境中發(fā)掘出隱藏的真實。“直接電影”的創(chuàng)作者則是拿著攝影機進入一個緊張的狀況而充滿希望地等待著危機的發(fā)生,在攝影機所拍到的事件中找到真實。不論是“直接電影”也好,“真實電影”也罷,追求“真實”是它們的共同理想,然而事實卻往往令人無限地失望。在紀錄片場景拍攝中,攝像機和工作人員的存在對現(xiàn)場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干擾力。被拍攝者可能因為攝像機的介入而改變話語方式和行為方式,乃至打破正常的人物關(guān)系,很多紀錄片創(chuàng)作者都會碰到這個頭痛的問題,攝像人員往往因為在尋像器里看到的一個不自然的微小動作而大失所望,攝像機在無形中抵抗著真實的進程。而事實上,我們并不可能還原絕對的真實,因為真實在紀錄片的制作中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創(chuàng)作者的誠實和良心之中。每個創(chuàng)作者可以根據(jù)他自己所相信的,他自己的感觸及經(jīng)驗,在他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定義真實,更準確地說,紀錄片的真實只是創(chuàng)作人員理解的真實罷了。任何創(chuàng)作都是主觀的,有誰能說教科書中的歷史是絕對真實的?在現(xiàn)場拍攝,不論是文化高和文化低的人,面對鏡頭都會顯示出某種超常的行為舉止,只是這種行為變化的大小有所區(qū)別而已。盡管人們認為經(jīng)過和對方的交流可以消除對方的不自然,但是要讓對方把攝像人員和攝像機當作空氣,那只能是創(chuàng)作人員的自欺欺人。尚·胡許在拍攝“真實電影”《夏日編年》時,當他把話筒伸出去的瞬間,“他便發(fā)現(xiàn)攝影機有種力量可以使人做出有別于日常生活的行為”。
三、“偷拍”手法的局限性
偷拍是指攝像師拍攝人物是在對方完全不知的情況下進行的,他希望在拍攝時不要影響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偷拍”這一手法在紀錄片的歷史中已經(jīng)很悠久了。“直接電影”主張的不干擾對象而采取的拍攝方式已經(jīng)是“偷拍”的成功先驅(qū)。如今中國的紀錄片創(chuàng)作人員也樂此不疲。偷拍也確實為紀錄片增色不少。電視紀錄片《龍脊》就有很多偷拍的精彩段落,學生與教師在課堂上溫馨而動人的場面,村頭村尾的村民們的日常生活等等。但在偷拍下的現(xiàn)實中,往往有一種“陌生化”的效果,人們希望通過屏幕看到發(fā)生在自己周圍的真實事件和真實過程,從而通過屏幕得到一種審美的安慰和愉悅,但是偷拍得到的只是一種淺存的表象,而不是現(xiàn)實的真實。正如蘇聯(lián)紀錄片大師維多夫所說:“攝影師不是要在現(xiàn)實中做個公正不偏私的觀察者,他應(yīng)該積極把自己埋入生活的門里,一旦他進入了,他可能明白‘事事皆有因’,這些即成為他影片中的主要意見。”有時偷拍很難進入到具體的事件中去,常常處于被動的位置。而且能偷拍到的題材和內(nèi)容是有限的,技術(shù)上操作的可能性,法律上的合法性都限制著偷拍的內(nèi)容。譬如,不能因為要表現(xiàn)愛情,而去偷拍別人親熱的場面。從觀眾的審美習慣上說也值得探討,因為這里有個人的隱私權(quán)問題。
四、紀實也要體現(xiàn)美
在紀錄片拍攝中,從頭至尾都在強調(diào)紀實,這根弦繃得太緊往往會產(chǎn)生另外一個矛盾,影像是否具備視覺美感。譬如拍攝一所農(nóng)家廚房,白天的照度都非常低,攝像機根本無法得到正常的細顆粒圖像,但這個黑暗的環(huán)境卻是主人公重要的生活空間。要紀錄這樣一個場景,“不干擾”對象是不可能的,所謂的“原生態(tài)”也是無意義的,因為這樣根本無法看到圖像。這時,就必須打燈。需要注意的是現(xiàn)場怎樣把幾個燈隱藏好,光線是否能讓被拍對象慢慢習慣,畫面上的光線效果是否能仿真,光線結(jié)構(gòu)是否合理。攝像人員在紀錄片拍攝現(xiàn)場是主動者,而不是受環(huán)境支配的被動者,因為攝像師的工作必須傳達一種符合視覺審美傳播規(guī)律的圖像。尤里斯·伊文斯在《攝影機和我》中談到:“重現(xiàn)現(xiàn)場給紀錄片的攝制引入了一個非常主觀的個人因素,導(dǎo)演的正直——他對真實的理解和態(tài)度,他傳出主題的基本真理的意志——他對觀眾責任感的理解……不包含這些‘主觀’因素,紀錄片的定義就是不完整的。”任何一種手段都是語言的工具,這種語言的使用要充分考慮觀眾的認可程度。“真實不等于自然狀態(tài),真實不等于粗糙”。
在跟蹤拍攝中,通常的方法是用廣角鏡頭。當焦距是9mm 時,視場角為98°左右,景物視野開闊,畫面比較穩(wěn)。運動時不易抖動,景深大,畫面內(nèi)信息量大。但同時,在運動跟蹤拍攝過程中,周圍雜亂的景物也進入畫面,如果離拍攝人物太近還容易產(chǎn)生變形。并且,這種“廣角畫面”在電視紀錄片中已成泛濫之勢,平庸隨之而來,藝術(shù)上的審美價值大大喪失。如果用16mm左右焦距的鏡頭拍攝,它的視場角比較小,接近人眼視場,畫面內(nèi)信息量集中,紀實的重點突出,只是因其用了中焦拍攝,在技術(shù)的操作上要困難些。它包括現(xiàn)場判斷、對事物的預(yù)見、精細地選擇拍攝時機和拍攝主體,焦點準確,熟練地運用器材以獲得穩(wěn)定而又具有美感的圖像等。好的攝像師是在不露痕跡的記錄中展現(xiàn)情節(jié)的,隱藏得越深,越能表明紀實手段的高明。
在現(xiàn)場,準確地控制景別和攝像機的運動,不僅能使記錄有重點有節(jié)奏,還直接關(guān)系到紀錄片的觀看情緒。要在“一次性”的事件中拍到完美的圖像,首先,對事情的發(fā)展需要有判斷預(yù)知,對周圍環(huán)境要熟悉。把畫面拍美,使它具有較強的視覺沖擊力是每個攝像師最起碼的職責,它和真實記錄并不矛盾。在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中,攝像師應(yīng)該是個相對獨立的個體,他應(yīng)該擁有獨立的判斷能力和能把這種判斷貫徹到底的權(quán)利。
- 上一篇: 定格動畫的發(fā)展與由來
- 下一篇: 專題片制作的包裝技巧